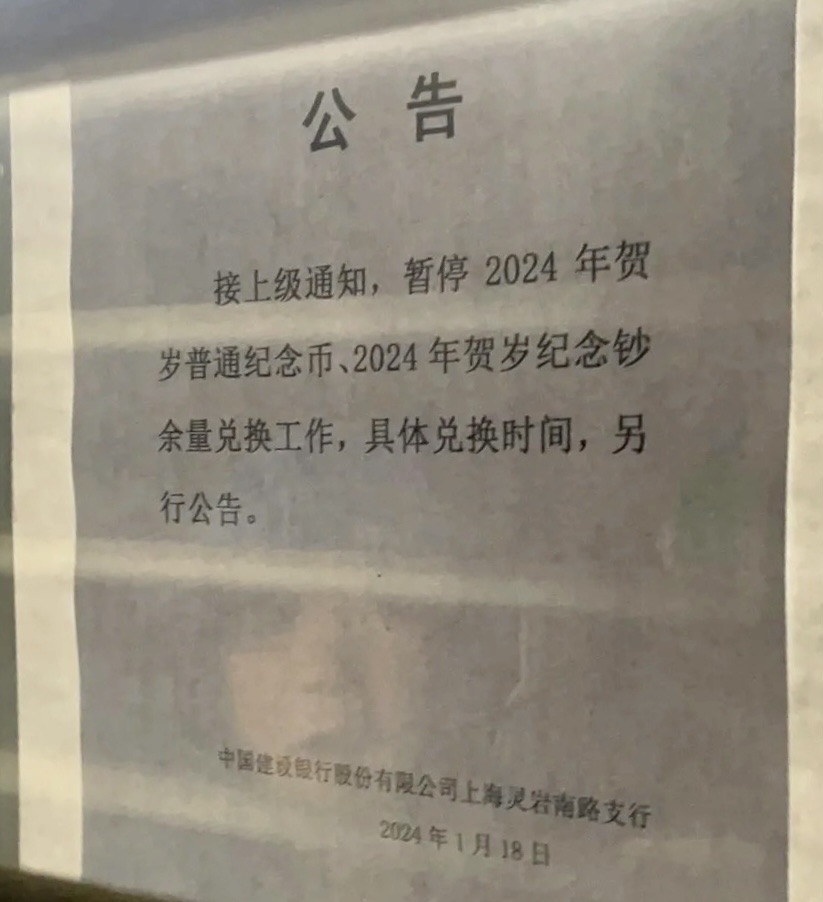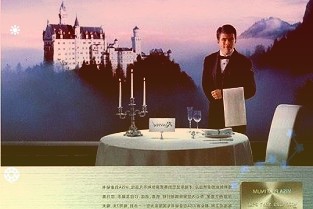韦应物《滁州西涧》是否有寄托
作者:徐楠
韦应物七绝《滁州西涧》,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一类读者只是爱重诗人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妙笔,沉醉于诗中的天机野趣。另一类读者的理解便与此相左。如谢枋得曰:“幽草、黄鹂,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已晚,不复光明也。末句谓宽闲寂寞之滨,必有贤人如孤舟之横渡者,特君不能用耳。”杨慎、黄生、章燮的诠释模式,均与此相类。这种认定该诗确有寄托的观点,在当代仍属常见。倪其心先生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幽草安贫守节,黄鹂居高媚时,其喻仕宦世态,寓意显然……(春潮带雨二句)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而忧伤的情怀。”(程千帆等主编《唐诗鉴赏辞典》之《滁州西涧》赏析文)黄天骥先生虽不主张将该诗用意如此坐实,却依然表示从诗中“可以看到韦应物牢落无助的心影”(《说韦应物〈滁州西涧〉》)。据笔者所见,“寄托说”在当下中小学课堂关于此诗的讲解中,也是屡被采用的。
《滁州西涧》到底是否在优美的景语背后别有寄托?追问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在追问合理地说明《滁州西涧》的寄托意是否可能?欲明辨之,首先需对该诗的文本表意特征细加分析。
先来品读“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要想判定这两句确有寄托,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幽草”、“黄鹂”(或“深树黄鹂”)在创作传统中具备稳定的托喻义,两句形成之文本语境具有明确的褒贬意味、反差效果。情况是否如此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某些物象或表达程式确有相对稳定的托喻义。当松、竹、梅、菊或“思美人”“嫉蛾眉”“浮云蔽日”在诗中现身时,读者心中油然而生“寄托”之揣测,并不属牵强。不过,“幽草”“黄鹂”似不在此列。《诗经·小雅·何草不黄》:“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郑笺以为“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方玉润从中读出“一种阴幽荒凉景象”。韦应物本人则在《贾常侍林亭燕集》中以“凌露摘幽草,涉烟翫轻舟”抒写士大夫雅集情趣,在《过昭国里故第》中以“池荒野筠合,庭绿幽草积”渲染感旧悼亡的气氛。不难看出,“幽草”在古人笔下并不专守某类寓意。既然如此,径把“幽草”(“怜幽草”)坐实为“君子在野”或“安贫守节”,就有我说即是之嫌。(按:此句“幽”异文作“芳”。古代诗歌中的“芳草”或“寻芳草”“怜芳草”在不同语境中或托喻理想,或托喻归隐,或表达惜时、恋物华等情思,亦不可一概而论)至于黄鹂(也即仓庚、黄莺),自《诗经》以降,便一直是古人表现生机勃勃之春夏佳景时常用的物象,且唐人尚常以“迁莺”喻进士登第、官职升迁一类美事。由此可见,恐怕并不存在什么以黄鹂为恶鸟、以之喻指“小人”的传统。而“黄鹂深树鸣”这一意象,或系从王维《瓜园诗》点染山中论道情境的景语“黄鹂啭深木”化出。一定认为其另有所指、尤其是“小人在位”之指,同样未免牵强。
那么,“幽草”“黄鹂”所在的前两句整体语境,是否具备某种特别的文外之意呢?倪其心先生分析道:“诗人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而对深树上鸣声诱人的黄莺儿却表示无意,置之陪衬,以相比照。”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解仍是存在商榷余地的。一则,一韵诗中,一句处理“仰观”,一句处理“俯察”,乃是古人空间描写的常见路数,该对比结构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抑扬意味。二则,“上有黄鹂深树鸣”是否上隶于“独怜”,或有见仁见智余地,但该句至少并未表现出对黄鹂的无视甚至厌恶。按古人常见写法,“但恨黄鹂深树鸣”或“何必黄鹂深树鸣”才会形成扬幽草而抑黄鹂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李日华《六研斋二笔》,“上”异文作“尚”。如果此句作“尚有黄鹂深树鸣”,那么倒确乎是在表达对黄鹂的喜爱了。三则,“涧边幽草”“深树黄鹂”并无强烈反差感、冲突感,很难令人联想到褒贬寓意,因此就更难令人把前者定向理解为“君子”、把后者定向理解为“小人”(或“居高媚时”)。与之相比,左思《咏史》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种描写,才是在意象间形成巨大张力的。即便不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云云承之,读者也自会察觉其中隐藏的褒贬意味与怨愤之情。
下面来看“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是否为“危难”“失遇”之喻,是否包含着“无奈而忧伤的情怀”呢?“春潮带雨晚来急”句中物象,在古人景语中均属常见。就如“幽草”“黄鹂”一样,“春潮”“急流”并不必然携带某种具体托喻含义。故而认为其实指某种具体人生境遇、社会环境,或许依然有失武断。至于此句整体语境是否蕴含动荡、危难等意味,且令“野渡无人舟自横”在其映衬下别有微旨,还值得多论几句。如黄天骥先生所说,“春潮带雨晚来急”的意趣,的确不同于“幽静宁谧”的“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不过细玩之,此句描写潮、雨之动势、力感,毕竟仅用一个“急”字,点到为止,别无渲染。且在常规想象中,西涧似非浩瀚巨流,“晚来急”亦到底不同于阴幽意味更浓重的“夜中急”。因此,“春潮带雨晚来急”固然未必是“幽静宁谧”的,却也终归与惊涛迅雨异趣,更和韦应物笔下“山郡多风雨,西楼更萧条”、“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登楼寄王卿》)这类鲜明地呈现荒疏、凄冷色彩的诗境大有不同。这样看来,黄天骥先生将其等同于“潮急雨骤”“潮水急涌而来,势如奔马”之境,进而据此将下句中的“舟自横”想象为“无人料理,孤孤单单,可怜巴巴,任由颠簸”(《说韦应物〈滁州西涧〉》),或许便略欠斟酌。再专门玩味“野渡无人舟自横”。“野”,郊外,离城市较远之处也,又常有真朴自然、闲散不羁一类含义,与“荒”“空”意趣并不完全一致。故“野渡无人”写出了远离尘嚣的滋味,又和情感倾向更加明确的荒凉、空寂一类情境存在微妙差别。而“自”字在古人诗中,常用于表现物象、人情自我经营、与他者无涉。此句中的“舟自横”,当然是具备这类意趣的,不过其表意终归到此为止,无涉其余。它和《诗经》中“泛彼柏舟”、《庄子》中“不系之舟”的关联,均在有无之间,难以辞逮。读者固然可从这样的意象联想到“不在其位,不得其用”或“无奈而忧伤”,但又何尝不能联想到“安闲自在,超然物外”等其他意味呢?
言说至此,已可发现,《滁州西涧》呈现给读者的,乃是虚灵、微妙、不落言筌的意义空间,而不是旨趣非此即彼的托喻结构。正因为此,一旦试图通过语义分析来确定某种寄托之意,就可能窄化其意义空间,也常难免有增字作解之失。值得注意的是,持寄托说的诠释者,通常还会动用“知人论世”之法。与韦应物创作《滁州西涧》直接相关的信息既已无存,则通过揭示安史乱后诗人沉郁、失落的时代病及韦应物在滁时“有志改革而无力,思欲归隐而不能”的个人心境来推论此诗深意,便是唯一可行之举了。可问题在于,人之精神世界并非时空中有形迹之物,且系世间最为幽深复杂、变化多端者。即便我们能够掌握明确记录《滁州西涧》创作动机的可信文献,也至多会得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诠释结论,难以如明镜映物般还原诗人所思所想。至于目前诠释者只能倚重的时代精神、个人典型心境,本就来自“简单枚举归纳”,系或然性推理的结果。以之作为大前提推测《滁州西涧》用心,结论自也是或然性的,且常陷入决定论的窠臼。当诠释者把作家“或然之意”认定为“必有之意”的时候,对《滁州西涧》的理解便可能受控于这类心理定向。于是在其眼中,不落言筌的诗篇,就越发显得别有深意;而文意解读时的独断,恐亦越发难以被其觉察。
总而言之,品味《滁州西涧》,读者当然可以“各以其情而自得”,生发出多种联想。但归根结底,无论从文本表意特征还是从与“知人论世”相关的现存信息特征来看,想要令人信服地坐实该诗“确有寄托”,都是不太可能的。通过本文的辨析,读者或许还可发现,若要使“探求寄托”这种诠释行为获得合理性,有几个基本前提当得到重视。其一,在缺乏可信文献旁证的情况下,对文本托喻义、隐指义的判定,应遵守“合惯例原则”。其二,应对文本在文献形态上可能存在的多样性保持警觉,尊重异文可能导致的诠释多元性。其三,应尽可能自觉地辨析与“知人论世”相关之文献信息的性质、效力、限度。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