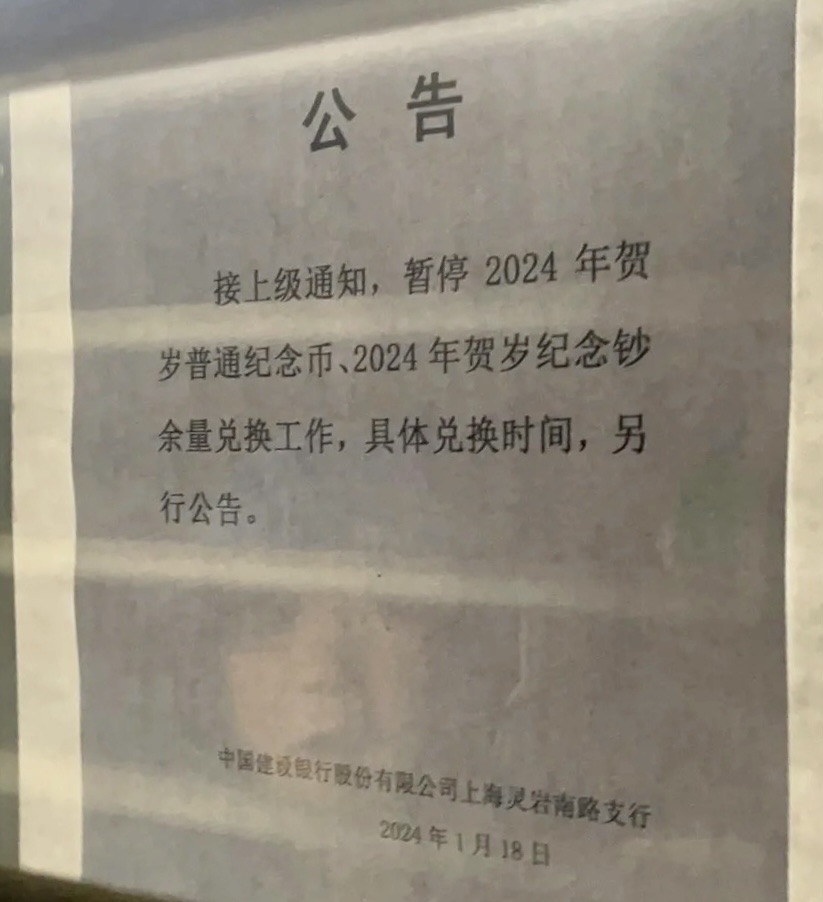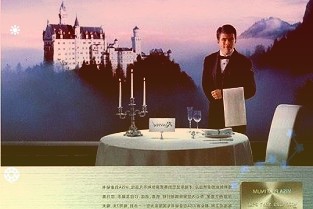上海与咖啡:过去、今天和未来交织的韵律
《上海咖啡:历史与风景》
唐之饴
据报道,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的咖啡店达到7857家,超过伦敦、纽约、巴黎,跃居全球之首。据说,目前上海居民人均每年喝咖啡20杯以上,年消费量比北京、广州、深圳的总和还多。可以说,咖啡早已融入了海派文化的基因。
破圈层:咖啡“征服”市民
咖啡当然是舶来品。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编纂《英华字典》时首度用“咖啡”翻译“coffee”。考虑到马礼逊曾于广州学习汉语,有学者推测,他是根据粤语音译的。1833年,另一位传教士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出现了“咖啡”一词。无独有偶,这份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同样出版于广州。
不过,没有迹象表明咖啡通过广州传入中国腹地,也没有记录显示当时有中国人喝咖啡。想来,咖啡应该是洋商随身携带满足自身刚需的。由于清政府将洋商局限在广州进行贸易,且严格限制其活动,规定他们只能同官商打交道,因此,洋商对咖啡的钟情不大可能突破圈层对普通中国人产生影响。
咖啡真正进入中国还是通过上海这个桥头堡,时为19世纪中叶。当时的上海滩华洋杂处,有利于外来事物弥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咖啡也不例外。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祖恩在新著《上海咖啡:历史与风景》中考证,上海最早的咖啡馆由西人开设,顾客多为西方侨民。此后,华人开的番菜馆将咖啡作为餐后饮品,据说食客只要喝上几口,油腻的煨鸽子、煎牛排就都消化了,堪称消食佳品。不过那时候咖啡不叫咖啡,而叫“珈琲”,除此之外,还有“高馡”“磕肥”“加非”等叫法,可谓众译纷纭。
名称的淘洗过程也是咖啡从市民偶一尝鲜的“海外奇珍”,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街头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尖,今四川北路、淮海中路、西藏中路都呈现出咖啡馆林立的景象。而咖啡馆主要的目标客户就是新兴市民阶层,包括商人、公司白领、作家、记者、戏剧家、律师等。
事实上,“去咖啡馆”之所以蔚然成风,和市民阶层强烈的内在需求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的聚会场所,无论茶馆抑或酒馆,如同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总是充斥着喧哗与骚动。市民阶层希望拥有相对私密的空间,或独酌,或聊天,咖啡馆恰好满足了这种愿望。幽暗的室内光线、自成一方天地的火车座、舒缓的钢琴伴奏,当然还有袅袅升起的咖啡香,共同营造出一个与市民趣味相匹配,并能供其进行社交活动的场域。由此可知,咖啡文化在上海的生成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基本同步。而在近代中国,上海是市民阶层孕育最早、发育最好的城市。
据《上海咖啡:历史与风景》介绍,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咖啡馆日益“摊头化”:不仅卖咖啡和西点,还搭售扬州点心、排骨年糕、鱼生肉粥等摊头小吃。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咖啡馆扩大客源的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咖啡已渗透市民的日常生活,喝咖啡不再那么讲究。抗战胜利后,咖啡摊犹如今日奶茶店,遍布街巷。这些摊头虽然设备简陋,但胜在现煮现卖、方便快捷。人力车夫跑累了停下来买一杯,几口饮尽,喊声“爽气”。此情此景,与意大利人以极短时间喝完一小杯意式浓缩继续赶路,相映成趣。
连人力车夫都用咖啡解渴,“爱喝咖啡”成为上海人的标签,其来有自,可以说“咖啡征服上海市民”。
双重奏:情调与理性
这种“征服”不仅是生理层面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层面的。毋庸讳言,咖啡初入中国是和西装、电灯、汽车一起被视作都市文明象征的。一个人不懂咖啡,自然会受到来自“都市”的嘲笑。《申报》登过一则段子,说某乡村教师误把芥末粉当成咖啡粉,请同事品尝,传为笑谈。名人亦不能幸免。老上海有谚:马崇仁喝咖啡,塞了牙啦。马崇仁乃京剧大师马连良之子,自己也是名角,只因在咖啡馆讨牙签,遭人调侃。
那么标准“都市人”怎么喝咖啡呢?陈祖恩教授几次提到的海派作家张若谷,即堪称样板。恰巧,孙莺所编《近代上海咖啡地图》和《咖啡文录》也收录了张若谷若干文章,让我得以拼凑出这位“咖啡馆铁粉”的大致样貌。
张若谷,上海南汇人,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回沪后任小报记者、主编,擅长散文随笔,小有名气。他给我的印象是:穿西装、戴礼帽,上衣左口袋永远装着一块白色方手帕,手里还拄着根司的克,几乎整天泡咖啡馆,观察记录,大量文字涉及咖啡馆的风物。其人与其文皆稍显做作。例如,他骄傲于自己懂法语,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咖啡馆,坚持用法语和只会说英语的俄国女招待交流,虽因此点错了咖啡,仍洋洋得意。
我一度不能理解张若谷的“凡尔赛”之举,后来琢磨,这其实是示范。张若谷向读者演示的不仅是怎样品咖啡、泡咖啡馆,更是如何从中获得乐趣。这是新兴市民阶层所需要的,今日流行的所谓小资情调,或许也发端于此。
但咖啡绝不是小资的专利,咖啡馆里也不全是张若谷。当年的上海咖啡馆不乏知识分子的身影,尤其是位于今四川北路、多伦路转角的公啡咖啡馆,由日本人经营,较为隐蔽,于是成了左翼人士的集散地,鲁迅、田汉、夏衍、郁达夫都是常客。“左联”开会也常设在此地。与之遥相呼应,原本开在霞飞路上的明星咖啡馆日后迁往台北,吸引了陈映真、白先勇、尉天骢等作家,他们相聚谈文学、谈理想。
在《黑金:咖啡秘史》一书中,怀尔德告诉我们,自1555年咖啡传入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便迅速传播,十年间开出600家咖啡馆。人们在这里分享信息,议论时事,辩难经典。无独有偶,18、19世纪的巴黎咖啡馆孕育了启蒙运动,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更是将咖啡馆、剧院、媒体,看作交流、平等对话的场域。当然,欧洲咖啡馆从不缺少张若谷之类人物,咖啡馆里向来上演着小资情调和公共理性的双重奏。
第三波:历史总是押韵的
说来有趣,哈贝马斯论述的18、19世纪欧洲咖啡馆和张若谷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咖啡馆,虽然相隔一两百年,从咖啡产业史的角度看却处于同一阶段——都以种植园生产为经济基础、以手冲为主要饮用方式。
据怀尔德所述,18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将咖啡树引入加勒比地区,凭借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劳动人口,咖啡和蔗糖、烟草一样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巴西,那里有大面积的种植园、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咖啡产量急速攀升。20世纪初,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90%来自咖啡业,顶峰时,巴西咖啡占据全球市场90%的份额。不难想见,当时巴黎、纽约、上海等地的咖啡馆,用的可能都是巴西咖啡豆。
那应该是未经烘焙的青咖啡豆,因为它能长时间存储,便于长途运输。相反,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只能保存数天,研磨则会让咖啡的细胞结构暴露于空气中,容易氧化,24小时后变味。所以当时的人如果想在家里喝咖啡,得先购买新近烘焙好的咖啡豆,然后研磨,冲泡,程序相当繁琐。像福楼拜、巴尔扎克这样一天能灌50杯咖啡的“狂魔”,家中绝对器具齐全且有专人伺候。普通人还是去街边店买现成的方便,意式浓缩和美式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开始改变。二战中,为了让前线官兵喝到咖啡,美军采用新工艺,生产易于运输和冲泡的速溶咖啡,受到广泛欢迎。据统计,二战期间美军每人每年消费速溶咖啡1.4吨,按美军总兵力计,速溶咖啡年生产量超过1500万吨。战争结束后,大量美国速溶咖啡以低廉的价格涌向世界各大城市,人力车夫在上海街头豪饮咖啡的场景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廉价且便捷,速溶咖啡短时间内便成为消费者宠儿。20世纪50年代末,速溶咖啡占据美国咖啡市场的三分之一,在欧洲也是高歌猛进,由此掀起了咖啡浪潮第一波。同时,速溶咖啡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效应有利于形成品牌,速溶咖啡巨头雀巢,就是在战后迎来高速发展的。标准化还让连锁成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咖啡连锁品牌。在全球化的推动下,雀巢和星巴克遍布世界,这被称为咖啡浪潮第二波,特点是品牌化和连锁化。
改革开放后咖啡文化重归上海滩,恰逢第二波浪潮汹涌,因此,像我这样的80后,对咖啡的认知是先被雀巢、后被星巴克塑造的。但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怀尔德就是位“咖啡原教旨主义者”,他坚持认为速溶咖啡是“类咖啡饮品”,对其多用罗布斯塔豆而非品质更好的阿拉比卡豆,以及粗糙的加工工艺充满不屑,有类似想法的远不止怀尔德。
2002年以来渐成趋势的咖啡浪潮第三波,表明这种诉求十分强烈。精品咖啡注重咖啡豆的品质和风味,崇尚“新鲜烘焙、新鲜研磨、新鲜炮制”,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向传统复归。不同的是,精品咖啡不依赖大种植园,而是直接与咖农合作,以避免价格倒挂,实现公平贸易。这再一次印证了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历史绝不重复,但总是押韵。
合上书本,漫步在今天的上海街头,看着方兴未艾的精品咖啡,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由过去、今天与未来交织而成的韵律?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