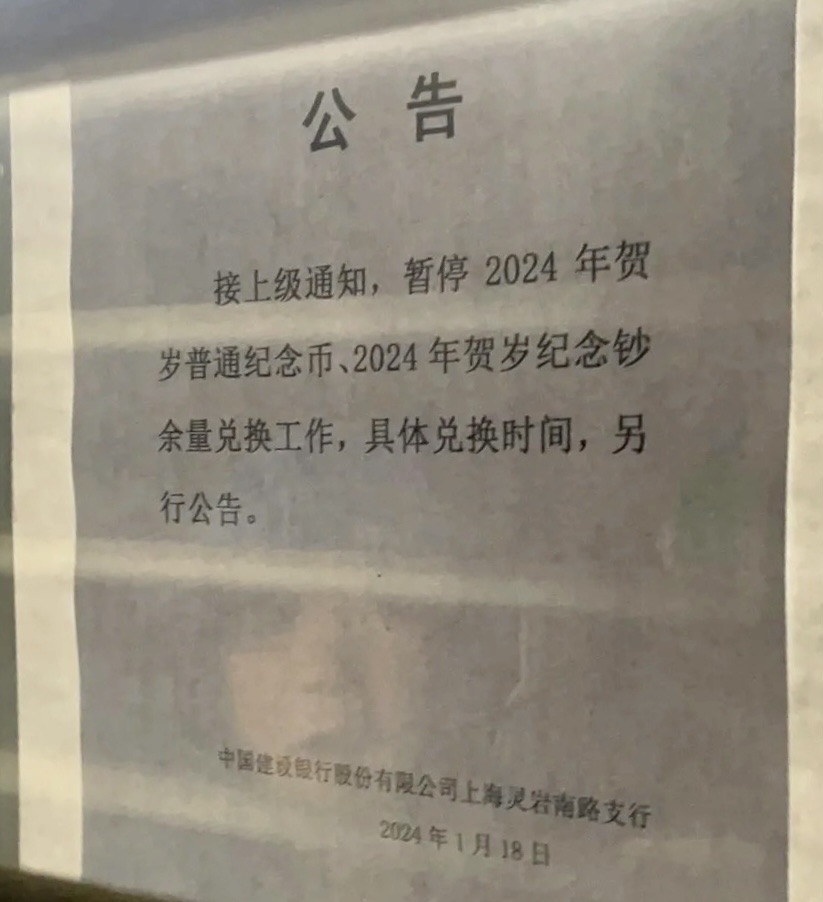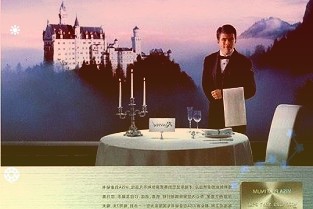作为“总体性”的王蒙——读《猴儿与少年》
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奇将历史看作是感性、动态且包涵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并寄希望于小说这一现代文学形式以达成某种超越,实现“总体性”的复归。
就当代文坛而言,王蒙是为数不多可以呈现并有能力实现卢卡奇哲学梦想的作家。王蒙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直至当下中国各个时段的历史大潮,他是作家、主编、批评家、文化与政治活动家,多重身份的叠合决定了他必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存在。而生命的长度、阅历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和激情的强度,使王蒙深入而丰富地介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文学生活,其长篇小说新作《猴儿与少年》,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耄耋之年的王蒙,站在个体人生的顶点,回望历史、俯瞰世事,深远宏阔的阅历与眼界,使其更易回归总体性的人间现实与历史理性。在《猴儿与少年》中,他的指点江山或自我抒怀,于无形中裹挟着历经风雨的复杂况味:幽默、揶揄、慷慨、豁达、较真、宽容等诸种富含生命质感的叙述姿态相互碰撞,交织为一体。小说安排主人公施炳炎和王蒙(耄耋老人)进行意识流式的跳跃性、片段式的谈话体叙述,一方面贴合老年人的思维特征与交流语态,另一方面以长寿之人的视点来完成对个体与历史关系的评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呈现出三个特征:时间久、体量大、穿梭自由。在时空的恣意穿梭中,人物主体既实现了对往昔的回忆、对当下的体验和对未来的展望,又不失时机地从一生体验中展开对历史及历史中人的总体性审视与评判。毕竟,很多细部的东西,唯有在更久远的回望中才可能真正闪耀出意义的光芒。
《猴儿与少年》关注的中心是人,它的反思性既体现在对过往历史的深刻洞察上,更体现在对历史主体的重新打量和裁定上。小说开篇回望上世纪50年代末时,摈弃了教科书式的冷漠评判,而代之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还原式展开与回望式品味,并辅以施炳炎青春个体的热情参与和切身体验。这让作品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质感和温度,散发出热辣辣的生活气味与时代气息,既有时人的兴奋、热烈、快乐、嫉妒和斗争,也有耄耋之年回顾往昔时的叹惋、和解、快慰与自哀。百年回眸,王蒙展现的不只是“青春万岁”,更意在阐明“生活万岁”与“生命万岁”。
《猴儿与少年》虽然篇幅不长,但颇具史诗品格,其中的主人公是活生生的丰满的人,呈现的是有机的火热的生活本身,其最典型的特质是家国一体,个人与历史浑然交融。一方面,人物的生命历程赋予历史以鲜活的形态和可感的温度,让历史以充满热烈与激情、纯真与挚爱的活泼面貌一一呈现;另一方面,历史也赋予个人主体性,给人以自豪、自信甚至自恋。在历史构筑的巨大风洞里,个人并非只是任由其裹挟的无奈的枯枝败叶,而是真挚地燃烧了自我、奉献了力量,这是王蒙的历史观,也是他在小说中希望表达的。
具体分析小说的主人公施炳炎,其历史主体性,鲜明地体现在从城市来到农村,在筑路、背篓中实现身体重塑的过程。他将1958年进山的这一天看作“新生”的起点,因为在这天的负重跋涉中,他猛然发现了自己“累不死也折不断的身子脖子关节四肢”,发现了自己坚强皮实韧性的“耐苦性”和“预应力”,他是“砸不烂推不倒碾不碎”的。随后在大核桃树峪的体力劳动中,施炳炎只3天“就感悟到了十根手指头加热、加粗、加力、加硬度、加生长”,劳动一周又发现了手掌上的坚硬茧子以及身体力量奇迹般地增强。这些慢慢苏醒的身体体验,意味着被压抑的青春的爆发与兴奋,沉重的劳动唤醒了生命的力之美,展示出虔敬的仪式感和救赎感,由此发现并熔铸了新的自我。在之后“最迅速、最自然、最放任随性痛快淋漓”的雨季造林中,主人公感受到的是“逍遥奔放、自由天机、恢弘驰骋,天地大美,道法自然”的人文“狂欢嘉年华”,让主体之美获得了进一步的大释放。
当然,这种历史主体性的凸显不仅体现在小说中人身上,而且发自作家肺腑。在一次访谈中,王蒙说:“我赶上了激情的年代,沉重的苦难、严肃的选择、奋勇的冲锋、凯歌的胜利,欢呼与曲折,艰难与探索,翻过来与掉过去……而我活着经历了、参与了这一切,我能冷漠吗?我能躺平吗?我能麻木不仁吗?我能不动心、不动情、不动声色,一式36.5℃吗?”这种历史主体意识的凸显,显然也是“耄耋少年”王蒙能写出《猴儿与少年》的原因。
《猴儿与少年》的宏阔与丰富还体现在文体的融会创新上,使得小说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互文性。融现代情境或文化意味于古诗词、歌谣而改之,骈散交织、戏仿频仍,颇有语言冲浪之感。小说结尾对2023年重返大核桃树峪的情景展开美好想象,既与书名“猴儿与少年”散发的青春阳光气息呼应,也表征着对社会未来的希冀与渴盼。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